
小堤咖啡。
為了撫慰昨日的情緒,今早又訪一趟。比起上次光臨時的熱鬧,這次只剩空調聲。還有翻報紙聲。
「今天比較少人啊?」我問。
「八點半就開始送早餐了,一批長青組的安親班已經走啦,都幾點了。」
其實老闆娘有點不悅我的蠢問題,我的確是趕11點早餐末班車來的客人,為了要在小堤舒服的打一篇文,早上洗了澡,通體舒暢的騎著單車裝作瀟灑的光顧。但其實她不缺我的瀟灑。
選了吧檯的位置,打開我的筆電。
「吃過早餐了嗎?」
「吐司要抹花生、奶油還是草莓?」
「散蛋荷包蛋?」
「咖啡冰的還是熱的?」
「黑咖啡還是拿鐵?」
「加糖嗎?」
我發現吐司果醬選項第一個她都會說花生,但我選了草莓。還有散蛋、冰拿鐵糖要多一點。她端到電腦旁,跟我說趁熱吃,但表情依然冷漠。
拿了一個切成對角的草莓吐司咬上唇邊,我選了甜甜的她來撫慰一早低落的心情,舌齒相抵讓她盡情翻騰,滿足肚臍裡的飢腸轆轆。然後再接一個酥脆三角形。
我總是不知如何吃乾淨未熟的蛋黃液,所以選了散蛋,就像我不擅打掃,所以把房子漆成灰灰的,差不多的原理。選讓自己心情舒服的,選筷子夾起來爽快的,即使灰灰的好似陰暗,但圍繞在水泥色下我就舒坦。即使荷包蛋滑嫩迷人,但我無法駕馭,散蛋夾在筷子上,舒坦。

「這裡開了多久呢?」
「你還沒出生就開了,比你還大。」她依舊冷漠頭也不抬的洗著她的杯子。
對比和長青組安親班熱絡的互動,她對新朋友似乎不那麼感興趣,就像福壽螺總是不受歡迎一樣,我可以接受這樣的對待,畢竟皮椅肩上的破損是她和他們一同經歷的,並肩作戰的戰友,總是相知相惜。而我只是福壽螺
吧台上的花,放置多久了,惹了一身落塵。我終究不敵她的冷漠,沒有勇氣再次開口問起每一個事物的歷史,儘管我對他們充滿無限好奇,而我只能繼續敲落鍵盤,當個襯職的福壽螺。


沖泡咖啡的動作持續反覆,翻閱報紙的長青組安親班孩子們閒話家常,說的是孩子、孫子、房子,或是政治、或是社會、或是台灣。罵啊,一定罵,還會摻雜幾句日語,無意識的說個幾句當年,在扯回現在。然後嘆口氣,啜口咖啡。
一個老朽開門進來,他們笑著說他今天比較晚報到,老朽坐在吧台前,掏了一佰,她為他送上餐點,連問都沒有的表現某種默契。我仔細品味著每個動作、每句話串起的故事。
到了這個年紀,是不是不再需要紀錄,而是倒數。老朽說那個誰的電話打不通了,他們就應和著「差不多了啦,也老了。」於是死亡在他們之間輕易的被討論著。我看著她右手舉高到咖啡的姿態,是不是,每泡一次咖啡,就倒數計時一次呢?
總有他們的默契,空調聲、歐西摩尼、脫漆的椅把、泛黃的牆面、蒸煮壺下的燭台,一切和諧的運轉在分秒間。她接了通電話,用日語說了「是是」,轉身拿起咖啡豆、又轉開瓦斯燒水。
「是熟客要來,他會先打電話。」她察覺我的好奇,兩句打發眼珠子裡的好奇心。我托著腮幫子想,她其實不太需要其他福壽螺造訪吧?裝潮流的那種福壽螺。就好比我。
和這裡格格不入的筆電敲完這些文字,闔上電腦後我會輕聲跟她說聲再見,我還是會當個格格不入的福壽螺。
然後你們就別來了: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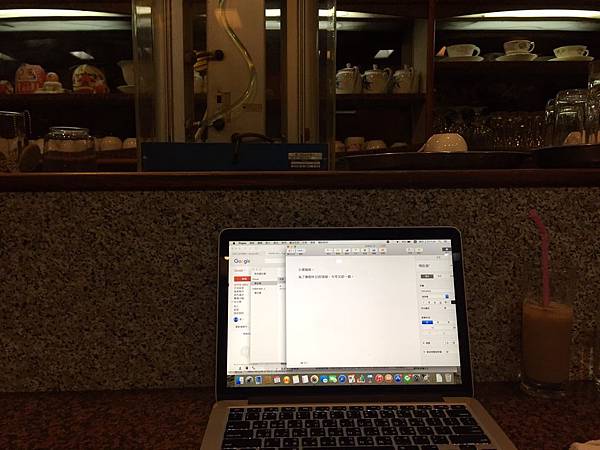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